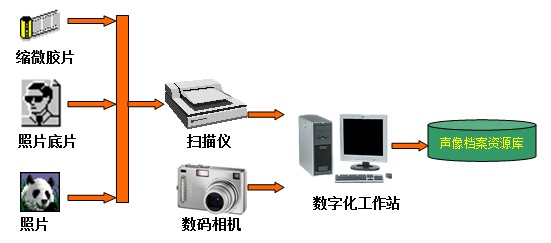历史上的编研成果形式
回顾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创造出“编研”这样一个词汇,却已经拥有了门类大致齐备的编研成果,上述抄纂、编述、著作三类成果可以说古已有之。
不少中国档案史和档案编研学的著作都认为,孔子编订六经开创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先河。特别是《尚书》,更被公认为典型的抄纂型成果。自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编修各皇帝圣训、王朝律令、大臣奏议等等,堪称绵延不绝。它们都可以归入抄纂型编研成果之列。
孔子对编研工作的另一大贡献是开创了编述型成果的编撰。《春秋》的内容出自档案,但经过孔子的笔削加工,不可能是原文照录,故而有所谓“春秋笔法”一说,大可视同今日档案人员十分熟悉的大事记。纵观中国历史,与《春秋》相仿,源于档案的史籍,如帝王实录,王朝的政记、会要、典章,还有成千上万的各种方志,所在多多。它们莫不是源于档案,而又以不同于档案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都可以将之归入编述型成果的庞大家族之中。
著作型成果也代有所出。一部《春秋》,被人嘲作“烂断朝报”,没有《左传》为它作注解说明原委,一般人无法卒读。《左传》作者左丘明是一位史官,他有条件接触档案,故能为《春秋》作注解。《左传》完全有资格被称为著作型编研成果。人们所熟知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与《左传》相比还只是后学。延至后世的官修史书,无不借重于档案,无不含有档案人员的辛劳,因此,把它们看作著作型编研成果,也有一定的理由。
中国古代以档案为主要来源的抄纂、编述、著作等多种形式的编研成果,可以说相当丰富。它们至今对丰富编研形式,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情况有所变化。特别从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档案编研工作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种档案文献汇编层出不穷,而其他形式的编研成果相对较少。从学界前辈,如刘鹗编《铁云藏龟》,罗振玉编《殷墟书契》,王国维编《流沙坠简》,到一些学者从国外抄录档案资料,如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变文集》,尽管各书内容不同,编者的目的、价值观等也有明显区别,但形式上都可归之于抄纂一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会编了包括11个专题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处开始编纂《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一个是聚集了众多史学大师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一个是后来在档案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权威机构,都加入了汇编档案的行列。现在回顾这六十来年许多人称之为编研成果的那些作品,给人以一个相当强烈印象的,似乎编研就是抄纂,就是档案汇编的代名词。
这个现象,不能用“好”还是“不好”作绝对的评价。它有贡献,确实让人们感到档案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引导人们重视档案。它还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嘉惠后人,证明了“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单从档案编研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带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汇编档案文献的高潮,所蕴含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个高潮让人感到兴奋之余,不能不想到历史上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这时候到哪里去了,这些作品虽然大量来源于档案,但档案工作者的身影却很少见到。
在近代中国,大概只有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可以具有档案馆的资格,继起的档案馆要一直到50年代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工作者的缺位自然是不难理解的。如果再来考察一下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更能看到这种情况同长期以来档案人员地位低下有关。殷周以降,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日趋边缘化。殷商掌管档案的巫和史,就是参与或者说是决定军国机要的重臣。但以后每况愈下,至有清一代,档案实际上被不入流的书吏掌控。所以到20世纪开始之际,档案人员已经没有能力来发挥档案所应具有的资政、存史、教化诸功能。这副担子不能不让别人来挑,让本来没有档案工作背景的一些学者来完成。
罗振玉以下各人能够在抄纂方面异军突起,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是学者,懂得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懂得档案的价值,也有能力体现档案的价值。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作为学者的他们,只可能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利用档案来推进自身的学术研究。因此,不能希望他们能提供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那不是他们的工作。而现在把他们的抄纂成果算在档案编研的头上,多少有点“掠人之美”的意味。还应该看到,他们大多为一代宗师,影响极大。宗师倡导于前,景从者响应于后,必然蔚成风气,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抄纂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可能也有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专家来华教授档案学的课程里包括文献公布学,这门课程成为日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一批抄纂工作者也加入了研究抄纂理论的队伍,以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既有成果显赫的实践,又有来头颇大的理论,抄纂的地位自然得到加强。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编研”这个概念,实在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这样的探索,一直到80年代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