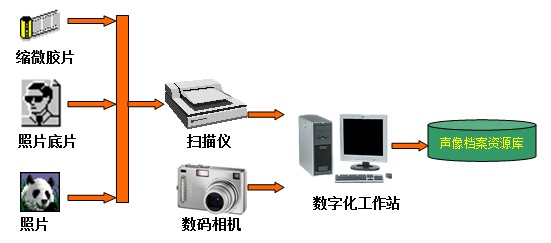档案文献编纂是一种特殊的著述行为
众所周知,各级档案部门的基础工作,是对档案实体的次序性整理,即对档案原件的收集、分类、排列、编目、鉴定,以及编制检索工具、进行统计、开展借阅等,这就是对档案的“第一次整理”。以“档案管理学”为代表的一些学科专门研究“第一次整理”的理论与方法。而档案文献的编纂与公布,则是根据一定的专题,在有关的档案部门内查选档案,经过严格的编辑加工,以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档案的信息内容,这属于对档案的“第二次整理”,即对档案信息的内容性整理,属于档案整理工作的高级阶段。
两次整理的共同目的都是方便读者利用档案,并有利于对档案原件的保护。“第二次整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围绕某一专题编纂公布档案文献,可以由以前档案部门“你来我调”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将档案原件编纂成各种形式的档案文献出版物,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对读者的主动式服务,使广大读者不用到档案部门调阅档案原件,就可以获得某一专题系统的、完整的和科学的档案信息内容,免去读者查阅档案原件的诸多不便,尤其还是使档案工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重要途径。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术特色在于,它剖析了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著述行为,既不同于学术研究的著书立说,也不同于仅仅是一种资料性的工作。档案信息不能直接进入编纂领域,不可能拿档案原件直接到出版部门去印刷成书,它必须通过编纂者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作用于编纂过程,如对档案文献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对档案文献鉴别校勘,对档案文献汇编内辅文的撰写,以及为了提高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及其成品的质量,而对档案文献编纂经验和规律的总结,等等。这都要求编纂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力:既要使得编纂公布的档案信息内容与档案原件记载的信息内容是等同物,又要使编纂出版物的档案信息内容通过编纂者的智力劳动得以有序化、社会化,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从而使档案原件的信息内容由自在状态,经过编纂者的努力,达到自为状态。
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著述行为,还因为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完整的学术活动,以编纂和公布档案文献这条无形链索,将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每个环节都体现了编纂者知识浸透在档案信息内容中的物化劳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绝非几件档案或几项编辑业务的简单拼凑,而是将史料价值较高的档案信息,凭借编纂者的慧眼,从档案实体中抽出,经过一系列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的编辑加工,生产出高质量的档案文献信息产品,从而使档案信息内容增值。讲授档案文献编纂学,目的就是让学生既获得档案文献信息方面的知识,又学到编纂者应具备的诸多与编纂工作有关的知识。
档案文献编纂学所面临的时代是以信息化为特征的21世纪,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即以档案实体管理为主转到以档案信息管理和档案信息服务为主,这个变革也必然影响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事业的发展。尽管经过50多年的奋斗,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学科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它毕竟是新兴学科,今后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作为学术工程的档案文献编纂,通过编纂者的学术性劳动,档案文献编纂在编纂者的主观努力下,成为一种特殊性的(即区别于单纯创作)著述行为,而编纂成品也就成为了特殊的著述作品,这是档案文献编纂区别于其他档案工作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