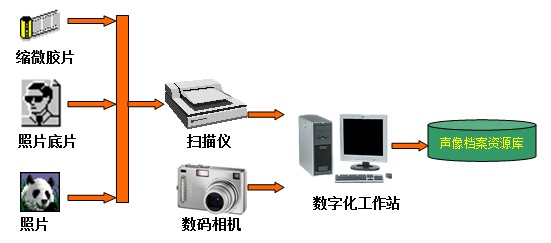档案的价值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是档案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档案理论乃至实践工作的基石之一。从大的方面说,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我们档案工作者乃至社会对整个档案事业的价值的认识,因为档案事业就是以档案为主要管理对象的一项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档案的价值就是档案事业存在的价值。从小的方面说,档案价值问题与许多具体的档案工作(如:档案鉴定、档案接收、档案定级等)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档案鉴定中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问题。所以,档案价值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档案界对档案价值的研究相当重视,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在众多的说法中,有不少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从总体上说,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观点仅仅是把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或国外档案学者的论点拿来改头换面就作为自己的成果了,缺少深入的思考、独到的见解,更缺少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相互印证。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力图结合档案工作的实际来进行档案价值的研究。
档案界对档案价值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就让我们先从这样一个定义开始吧!据《中国档案》引自“Harrod’sLibrarians’Glossary”(第五版)中的档案价值的定义:ARCHIVAL VALUE:The decision,after appraisal,that documents are worthy of indefinite or permanent depository.⑴冉也先生对此的翻译是“在对文件鉴定之后做出的值得无限期和永久保存的决定(注:准确点说,这一术语应译为‘具有档案性质的价值’,对应中国档案中的‘永久价值’)”。翻译的水平很好,但问题是这个定义本身,无论从“档案价值”去理解,还是从“永久价值”去理解,似乎都让人有循环定义的感觉,因为从他的定义中难以发现有不同于被定义概念字面意思的成分,难以让人对这个概念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因此,我们对档案价值的研究应该避免类似的错误。
一、档案价值的范畴
有一类观点认为,档案的价值是劳动价值,认为档案价值也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笔者难以认同。首先,且不论档案以及档案的前身----文件是不是劳动产品或者商品,而且即使从可行性上说,档案的价值量也无法从劳动价值、从社会劳动时间的角度去衡量。试举一例:上海市档案馆有一份珍贵档案《上海市军管会关于接管上海的布告》,该布告是解放军占领上海时发布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该档案的社会意义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上海的胜利,标志着三座大山在上海的推翻与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分水岭。但是,如果从劳动价值的观点去看,创造这份文件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什么呢?大概只能是制造这份文件所用的纸张、笔墨的时间加上这份文稿的拟制时间吧!但这样计算出来的价值量能反映出该档案的社会意义吗?显然不能。如果硬要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衡量这份档案的社会价值,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用了多少劳动时间?推翻三座大山用了多少劳动时间?时代的分水岭又可算作多少劳动时间?好像难以计算。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劳动时间可以以共产党存在的自然时间计算嘛!但这也不科学。因为上海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只存在了28年,若以此为劳动时间,那么,共产党的价值可计为28年。可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存在了几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劳动时间就应以千为单位去计算。这样一比较,难道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倒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了吗?而且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那么烈士们的头颅一颗值多少劳动时间?热血一千克值多少劳动时间?总的加起来又值多少劳动时间呢?
再说,要计算推翻三座大山的价值量,仅从推翻去算还不够吧?还应该以三座大山的创造价值为衡量的基础才显得出一种对比的意义,那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用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呢?不把这些算清楚,又怎么能说清《上海市军管会关于接管上海的布告》这份档案的社会价值呢?所以,正因为大多数档案的社会意义、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牵涉面太广,它是难以用定量计算的。特别是历史价值,因为历史是无数事件在无尽的时间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一件事的历史价值是环环相因的,可以无限追究下去。
而且档案中需要评价价值的因素很多,比如时代、事件、人物等等,上面已考察过时代和事件的价值衡量方法,再考察一下人物。许多代表性人物,其价值量也难以用劳动价值去衡量。比如,《黄金荣悔过书》也是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珍贵档案,它是黄金荣----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的流氓大亨在解放后向政府和人民表示忏悔的一份自白。且不说这份文件的时代意义,就单说黄金荣这个人的劳动价值量----即创造这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怎么计算呢?是算他妈妈把他养大所用的时间和开销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劳动时间和开销?如果是算他妈妈把他养大所用的时间和开销,那么,每个人的价值都差不多,又怎么体现出名人的独特性?再进一步问,黄金荣变成流氓用了多少劳动时间?变成大亨又用了多少劳动时间?我看这些都很难计算吧!更别说加上这份档案的时代价值的计算了,因为这份档案与上述《军管会布告》具有同一时代价值。所以,这是运用劳动价值论去衡量档案价值的必然失误。如果要这么去计算,我看许多复杂文件的价值量大概要用大型计算机去计算了。附带说一句,所谓档案价值的定量分析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只要看一下《档案工作实务全书》中的定量计算公式⑵,就可以知道,这种看似科学客观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可以使用了。一份档案尚且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计算,更何况档案鉴定人员要同时面对成千上万份档案。
综上所述,档案的价值不应该属于劳动价值、商品价值等经济学上的范畴,不应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衡量。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档案的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即是档案客体对人们主观需要的满足程度。这种观点的典型说法就是“档案价值是档案对人们的有用性”。这种说法是直接引进了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⑶应该肯定的是,它对我们认清档案价值的真正归属有很大的意义,避免了档案价值与商品价值、劳动价值混淆不清的失误。但是,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这种定义仅仅是一种哲学价值理念的简单照搬,对档案价值的解释过于空泛,内容阐述抽象,远离档案工作实践。⑷其实,何止档案,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如此,都是对人们的有用性,所以,这种定义没有档案特性,没有准确到位地揭示档案的价值。从定义的基本要求----种差加属概念来看,这样的概念只有属概念而没有种差,因为它没有指出档案对人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有用性,所以,也就不能真正说明档案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明确,档案价值属于哲学范畴。这是我们考察档案价值的出发点。
二、利用决定论辨析
从档案价值的哲学范畴出发,有一类被称为“利用决定论”⑸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国内外都有。其中有种具体说法认为:“档案的价值是档案与主体----利用者对它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是指档案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是否满足主体(即利用者)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档案也只有与主体的需要发生关系时才产生或表现出价值。如果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档案根本不被人们需要和利用,它们就毫无价值可言。”⑹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档案价值判断中必须遵循“主体原则”----也就是以利用者为主进行档案价值判断的原则。笔者极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本身不符合事实。而且如果档案鉴定的实务工作真的以此为指导思想,将会导致档案价值判断的混乱以至档案鉴定工作的极大失误和实际上的无法操作,因为利用需求的偶然性、片面性、多变性、无法预测性以至不可知性,将使鉴定工作在实际操作的层面难以进行。以下具体论述。
第一点,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如果档案“只有与主体的需要发生关系时才产生或表现出价值”,那么,谁是档案价值的创造者?照上述引文说来,档案的利用者成了档案价值的创造者了?显然,这不符合事实,这等于是在颠倒档案价值产生的历史次序!是先有文件和档案的存在,而后有利用者!而不是先有利用者,后有文件、档案的产生!事实上,从档案的前身----文件的产生之日起,其价值已包含在其中了,而并非是由以后去利用档案的人赋予它的。
即使在他自己的表述中都可以发现矛盾与混乱之处:“档案也只有与主体的需要发生关系时才产生或表现出价值”。请注意他的表述:“产生或表现出”,那么到底是产生还是表现出呢?因为他认为主体是利用者,所以,“产生”就意味着利用者是档案价值的创造者,但这已说不通。那么,如果是“表现出”,其潜在含义就意味着在利用之前,档案已经具有了价值,只不过是通过利用者,将价值发现出来而已!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说明说这句话的人大概自己也没想清楚到底利用者在档案价值中起何种作用。
其实,利用者不是创造档案价值的主体,只能说利用者是发现档案价值的主体!档案是在利用时表现出价值,而在利用之前,档案已经具有了价值,只不过是通过利用者,将价值发现出来而已!档案是否具有价值并不以利用与否为转移!档案价值是个客观概念!因为档案的价值早已由文件的形成者创造出来了。
库藏的档案不被利用,并不能说明其无价值,而只是说明其价值还未被发现罢了。如果“如果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档案根本不被人们需要和利用,它们就毫无价值可言”,那么在现在的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的大多数档案就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掉了!现在的档案工作的大部分就都是毫无意义的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极为短见的。保存着而未被利用过的档案,将来总会有被社会利用的一天,总有在社会上发挥它们价值的一天!有许多鉴定事实可以说明,有人从一时的利用需求出发,鉴定备毁了许多当时认为没有价值的档案,但一段时间后,发现备毁档案中许多又有人要利用了,再忙着修改鉴定结果。这种失误就是以利用决定论为指导所造成的。所以,在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鉴定理论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备受批评的档案“鉴而不毁”现象倒不仅不是一件坏事,它实际上是防止造成重大鉴定失误的一种必要措施。
第二点,设想一下,果真从利用决定论的观点去认识档案价值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过去或现在有人用过某一份档案就说明它有价值,而过去或现在没有人要用的档案就一定没有价值,那么,岂不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同一份档案如果今天有人用就有价值,明天没人用又没价值了?或者,因为它过去或现在没人用过,就认为它没有价值而把它销毁了,但是,明天有一个人来要用,它又变成有价值了,可是这时它的尸骨也已荡然无存了。而且,一份档案即使以前有人用过,又怎么能一定推断出将来也一定会有人用呢?反之,一份档案即使以前没有人用过,又怎么能一定推断出将来一定不会有人用呢?因为天晓得哪份档案在哪个时候会冒出哪个人来用!所以,以利用来说明档案的价值将永远说不清。
在实际鉴定工作中从利用出发将难以界定档案的价值,还因为对鉴定人员来说,利用者的概念本身是不确定的,是由多种类型组成的。不同的利用者的利用需求是不同的,甚至对同一份档案由于利用需求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对它的价值判断的结果也就会不一样,某一份档案对某个人无用,可能对其他人仍然会有用。有一种经典的说法是“有些人把大量的文件说成废物,但是一个研究者的废物可能是另一个研究者的珍宝。”⑺
而利用者,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人去看,其利用需求是偶然的、片面的、多变与不可预测的,利用需求无规律可寻,因此,根本无法预测。利用需求永远都是即时发生、偶然发生的。这一点,无论在一段历史时期中还是从无尽的时间发展上看,都是这样。
研究一下历史上的利用高潮的情况可能会使我们对利用需求发生的偶然性有更直观的认识。我国在7、80年代,档案利用需求的主流是落实政策,8、90年代是编史修志,90年代后是经济建设。这些利用需求都是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突然发生的,是人们为完成某项突击性工作、满足某种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大规模利用活动。但是,在这些利用需求发生的几十年前,甚至仅仅10年前都不可能预测到这些利用需求。比如,在文革中不可能预测到档案将来要起落实政策或编史修志这种功能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更不可能预测到将来会以经济建设为利用的中心。若基于当时的利用需求就把经济建设的档案全都销毁,那么到了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时期我们将无档可用!这些利用高潮的发生,它们大都来无所从,不知何时会来,它们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也就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任何一个时期的利用需求不可能涵盖所有时期的利用需求,不可能涵盖无尽未来的利用需求,因此就无法准确反映档案利用需求的全部。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档案利用需求因此也就具有了多变性。从上例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利用需求有很大的变化和差异,所以,我们不可以“刻舟求剑”式地以一时一地的利用需求涵盖所有的需求,并以此来评价档案的整体价值和一份档案的具体价值。
实际上,如果要从档案利用的角度去衡量档案的价值,那么档案的价值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无法穷尽的。我们现在已知的档案利用价值就有:凭证查考价值、历史研究价值、文化价值、鉴赏价值……不一而足。作为一种原生性历史记录,档案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不仅是“行政管理的查考凭据,生产建设的参考依据,政治斗争的必要工具,编史修志、科学研究的可靠资料,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的法律书证”⑻,而且从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研究政治学、历史文学、公文程式、书法艺术、关防印章、邮票、证章等等。人们对档案利用价值的发现和认识,是随时间的推移和时势的发展逐步变化和深化的,所以,档案不仅有我们现在已知的种种作用,还会有许许多多潜在的作用我们尚未认识到。档案虽一,妙用无穷,用列举档案利用需求的研究方法去认识档案的价值又怎么讲得清?如何会具有科学性?这种方法至多能认识档案即时的各种具体的利用价值和使用价值,连档案的所有利用价值都无法认识完整,又怎么能认识档案的根本价值呢?
以利用的倾向为指导,档案的价值根本无法被彻底认识,鉴定工作也就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利用的因素是如此多变,令人无法把握。只从当前的实际利用需求的某种倾向去决定档案的去留,将来一定会在新的利用需求面前傻眼。有一句诗正可说明问题:“我不知道风会在哪个方向吹”。档案人员不是神仙,不可能知道档案利用之风何时会向哪一个方向吹,所以,只强调唯利用之风是从,将来一定会被风耍。
因此,利用需求实际上具有不可知性。如果把鉴定工作比作求解数学方程式的话,应该根据一个已知条件去求得一个未知数,即从一个已知的鉴定要求或需要,去决定鉴定结果----每份文件的去留。但是,由于将来利用需求的如此多变以至于不可知,我们又怎么能根据一个未知数----“将来的利用”去求得另一个未知数----“鉴定结果”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利用决定论不能科学地反映档案价值,不能用来指导档案鉴定实践。
还有一种变相的利用决定论。有人主张档案价值应依据公众舆论来判断,以此来体现社会决定档案价值的观点。德国人布姆斯就曾经认为是“社会而非历史学家或文件形成者决定了档案的价值,因而也决定了档案的重要性和档案的保管期限”。⑼所以,他主张要依据公众舆论来判断档案价值,进行鉴定工作。应该承认,档案价值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且这一点很重要,这关系到如何认识档案价值的主体的问题。笔者认为,档案价值的主体应该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概念不清的利用者。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考察档案的价值,得出的结论才会符合档案价值的实质与本质,但是,社会不应该等同于公众舆论,不然,又会成为变相的利用需求决定论。因为公众舆论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公众产生的,其性质与上文分析的利用者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它同样具有偶然、片面、复杂多变与不可预测性。而社会决定档案价值的这个“社会”应该是客观意义上的社会,而非主观意义上的社会,不是公众舆论----这种即时发生又不断变动的社会利用需要,而最起码应该是社会对档案的根本需求或长远需求,这样才能科学地界定档案价值。事实上,布姆斯本人以后也认识到公众舆论的不可靠,自己放弃了这种说法。这也可佐证利用决定论的行不通。
当然,利用需求在价值鉴定中也不是没有一点作用,因为档案的价值量有时并非表现得那么明显,而利用需求能“表现出”档案的价值,所以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衡量档案的潜在的价值量,对我们鉴定工作有一定借鉴、启发和参考作用。但是,它在鉴定中只能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而非主导、指导地位。
三、客观说的不足
与利用决定论者认为的档案价值具有主观性的观点相反,有人认为,档案的价值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⑽。他们认为,档案的价值是多元的,以往对档案价值的研究往往是注重其利用价值,即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而比较偏废档案作为一种物体存在的客观的自身价值。他们认为,我们对档案价值的观念必须要转变。因为档案的自身价值是由其自身因素造成的客观实际决定的,我们完全可以就某一具体的档案做出价值判定,而不必过多地去考虑社会其他因素。档案的价值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不因人们的是否利用而左右,社会的利用只是该档案的价值得到了某种体现,即使社会不去利用,它的自身价值仍然是客观存在着的。档案的自身价值只有通过利用才会最终得到实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并不排斥档案作为一种存在物体的自身价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着。只有这样,档案的价值才能与文物等一样得到社会的认同。
笔者认为,档案价值客观说符合实际情况。确实,如果社会要用档案时我们的档案与档案事业才有价值,社会不用时我们的档案与档案事业就没有价值,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存在价值的客观性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价值是要别人来赋予我们的!我们自己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虽然说档案价值具有客观性,也并不否认档案价值是与人的认识有关的,它不是纯自然的物质。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领域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事物与规律存在。档案的价值也应该是这个范畴里的。所以,笔者赞同档案价值客观性观点。不过,遗憾的是,这种观点仍然没有揭示档案自身价值到底是什么。
四、双重价值论的优劣
目前,关于档案价值的学说,最被广泛接受的是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由于笔者资料之限,无法看到谢伦伯格本人对档案价值的完整表述,所以,只能参照他人的翻译转述来进行研究。根据《外国档案管理》⑾一书的介绍,谢伦伯格认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文件的第一价值(又称原始价值)指文件对其形成部门工作事务的有用性,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文件的第二价值(又称从属价值)是指文件对形成机关以外的其他利用者的有用性,包括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统称档案价值。
谢伦伯格的观点确实有精辟之处,因为他把文件的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即档案价值)分开,也即把文件与档案的价值明确地区分开来。明确了档案价值是对形成机关以外的其他利用者的有用性,肯定了档案的价值是一种对社会的有用的价值,即档案价值的社会性。对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的区分,又分清了档案的主要作用----证明机关历史与其他作用----参考作用。而且对档案证据价值的揭示,直接导致了对机关职能在鉴定中的重视。
但是,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并非完美无缺,例如:美国人戴维·比尔曼认为“传统鉴定是以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作为衡量文件丧失现行价值后是否需要保存的主要标准,但它们存在严重缺陷。”⑿库克在13届档案大会的报告中也对此作过批评性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情报价值。
笔者认为,谢伦伯格把文件价值划分为第一价值(文件价值)和第二价值(档案价值)很正确,但在对第一、第二价值的内涵的定义上都不清楚,用的是定义不周延的列举法,没有注重从第一、第二价值的本质属性上去把握。特别是把档案价值仅仅定义为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有其片面性,因为这些仍然还是档案的使用价值,不能完全涵盖档案的所有使用价值,更不是档案对社会的根本价值。所以,他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是有一定的欠缺的。
第二,谢伦伯格对情报价值的研究方式有问题。他对情报价值的定义是“公共文件内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的情报资料。”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无可厚非,但在对情报价值的鉴定方法上,谢强调道:“他(笔者注:指档案工作者)也会保存那些含有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所需情报的文件,这自然要以他能够确定对于它们的保存确有某种需要为限”⒀。由此出发,他认为:“在鉴定文件的情报价值时,还可以考虑到各种研究上的利用。进行这种利用的可能有:各种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关心纯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以及关心纯人事问题的家谱学家。”⒁在这里,我们明显感到,谢伦伯格是在用列举法来定义利用的需求,他已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利用需求决定论”的失误中去了。事实上,“利用决定论”最早出现在谢伦伯格提出“双重价值论”之后的美国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谢伦伯格提出的研究“情报价值”的方法继续延伸和发展的结果。因此,谢伦伯格的双重档案价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从证据价值出发,档案价值具有它存在的客观性;而从情报价值出发,档案价值却又具有任凭具体利用者涂抹的主观性。所以,只要是忠实地照双重价值论去实施鉴定,都逃不脱这对矛盾。比如: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通过的《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4条:“档案工作者对文件去留的选择,首先要考虑保存那些反映文件产生或收文机构和个人主要活动证据的文件,但也要考虑利用者的变化需要。”⒂这里的“考虑利用者的变化需要”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捉摸,更别说实际操作了,具体理由在前文已述。
笔者认为,其实,情报价值确实存在,但不应该用谢伦伯格的方法----利用需求决定论去判定。因为,情报价值也具有其客观性,不应该单从个人利用的角度去考虑,鉴定情报价值也必须考虑机关的职能,避免随意处置涉及个人的档案,因为个人利用的对象也无非就是在机关职能活动中形成的文件和档案,它们是客观存在的。
五、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几类档案价值定义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它们对我们进行档案价值定义研究时的有益启示有以下几点:首先,要避免定义的逻辑错误。定义必须严格遵循逻辑规律,不能犯循环定义、缺少种差、用不周延的列举法来定义概念的全部内涵等等错误,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律去做,清晰地将档案价值的内涵揭示出来。
其次,不能犯认识论上的错误,对档案价值概念的认识不应该有主观随意性。确实,档案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属于人的认识领域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价值就具有了主观随意性,是可以“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因为认识领域同样存在着客观规律,例如真理问题。真理是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反映,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要具有正确性就必须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性,而并不是说真理就是可以任凭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东西。同理,档案的价值是人们对档案这个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对档案价值的判断也不是仅仅可以靠人的主观随意性就可以决定的,档案价值要判断正确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档案客体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档案自身属性的深刻把握上。
第三,在认识主体上,不能用含糊的“利用者”概念代替整个社会作为档案价值的认识主体。确实,档案价值是档案的有用性,但是,它是对谁的有用性必须先搞清楚。对主体的表述不能用“利用者”这个概念,原因是“利用者”概念很模糊,从它出发,很容易变成对具体的人、部分的人群的考察,而个人或部分人(如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图和利用需要并不能代表社会整体的意图和需要。虽然笔者并不否认,从具体利用出发去考察,可以发现档案的种种使用价值,可以发现档案提供具体利用的种种方法和途径,但这并不能代替对档案价值的本质的认识。不可否认,个人档案的价值主体是个人,个人有根据自己需要自主处置的权利。但是,只要是公务档案包括个人档案中作为社会活动记录的那部分,其价值也即有用性,就应该是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有用性,我们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档案价值的主体去考察,应从这个角度去揭示档案价值的本质。笔者认为,档案,特别是公共档案,对社会的根本价值是社会记忆价值,具体论述见另文。
注释:
⑴转引自2000年第2期的《中国档案》英语角
⑵陈兆祦、王信功、刘振淮 主编《档案工作实务全书》,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316-319页
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版)第4册,第306页,“价值学”词条。
⑷2000年10月《中国档案》,陈忠海《从鉴定体系看档案价值和档案鉴定概念》。
⑸[加拿大]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
⑹同注2第302页。
⑺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83年版)P161
⑻冯惠玲《档案管理学》(1999版)第14页。
⑼《中国档案》2000年第5期第44页
⑽《中国档案》2000年第1期严永官《馆藏档案分级管理的几个问题》
⑾韩玉梅、黄霄羽主编《外国档案管理》1998年版第17、107-110页
⑿转引自黄霄羽 张宁《宏观鉴定战略在加拿大的应用》,〈中国档案〉2000年第8期。
⒀同注7第38页。
⒁同注7第161页。
⒂转引自徐玉清译《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档案》1996年第11期。